1、余英時的方法: 實証與詮釋,交互為用。實證(考證)以求古人之心,所謂「詮釋」在「善解古人之言」,廖肇亨,溶實証與詮釋於一爐,寫在「方以智晚節考」初版發行五十年,閱讀余英時, P.11)。這和辦理法律案件的「考証」(證據)和「詮釋」方法頗相似。是要「善解」?還是「悪解」?建議儘可能公正啦⋯⋯
2、再找時間讀「柳如是別傳」(陳寅恪)、「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二書均在考証與詮釋明末清初文人的內心世界。余英時說他寫書時,陳寅恪的書尚未出版,他和陳寅恪同心。
3、「、、且東原於義理之転變,自尊朱而排朱終至詆朱子,雖有其自己在義理上之領悟,然在実齋看來,適所以見其心術之不正。其故在於東原飲水忘源,乃至批判朱子以取悅於衆狐狸。對照於實齋之堅強所守而不為世人所知所重,則東原行徑招來實齋之譏,良有以也」(蔡長林,思想史的內在理路——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遺產。閱讀余英時,P.20)。 這項「批判」很重,是耶?非耶?先札記之。戴東原曾說「言之深入人心者,其害於人也大,吾不知民受其禍之終極」,給我印象深刻。引自胡適,戴東原的哲學。
4、錢穆不願接受「新儒家」?
余英時是錢穆在香港所創辦新亞書院的第一期學生,錢先生於91 年過世,余英時以長70 頁的文章說明「錢穆與新儒家」,一、結論: 錢穆不願接受新儒家;二、經對「新儒家」為語言分析,有三義:(-)任何20 世紀學人,凡對儒家不存偏見並認真加以研究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余英時認為似乎已擴大到沒有什麼意義的地步了。我不敢苟同);(二)以𠵍學為取捨,只有在哲學上對儒家有新的闡釋和發展的人,才𠕇資格取得「新儒家」的稱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可以算是。日本島田虔次也以哲學為標準。(三)即熊十力學派中的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𠕇私淑熊氏之學又為熊門認可的,如聶雙江之於王陽明,當然也可居「新儒家」(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P’60、61);三、余英時認為錢先生為學旨在「打破門戶」,成為「通儒」(P.32-34); 以上第一種用法空洞無意義,決非他願接受; 錢先生無意走𠵍學道路,也不是第二種「新儒家」(P.63) ; 錢先生更不是第三種的「新儒家」,他們雖是論學之友,但見解頗多不合,熊先生在理學上特尊陸王,熊先生之成為開山祖師是他的弟子第二代新儒家近四十年來在海外開拓了新領域,最關鍵的是1958 年的「宣言」簽名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先生(P.68) ; 錢主張「陸王之學為理學之別出、、只拈一字或一句來教人、、終久大之易簡工夫,已走到無可再易再簡,既已登峯造極,同時也是前面無路」(P.70-72;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P.88) !
呂律師以呂祖謙邀集朱陸於「鵝湖書院」」欲融合理學心學的觀點認為錢穆是「大儒」、「通儒」,著有「朱子新學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等大書,雖兼史學,就像呂祖謙也精通經史,自然仍是儒家,至於新不新只是次要的形容詞。民國儒家少不了錢先生。至於「新儒家」的第二、三種用法,意圖獨佔語言,甚至引起誤導,似不宜。或稱「熊門新儒家」較合宜,既懂哲學應懂語言分析、分析𠵍學。此種紛爭証明1175 年鵝湖之會的用意,竟至2024 年還有深刻的現代意義與價值,800 多年來至2024 年的理學、心學紛爭,浪費了許多民族的精力,應回顧「鵝湖之會」融合的深意。
李惠君:
「時儒」也!
我非常認可毓鋆老師所言:「應是時儒,‘’學而時習之”,達到最高境界,即聖之時者。」
若以「時儒」定義,那末,時代裡,能如是者,即是時儒,無新舊之別。(毓鋆,毓老師說易經,電子書P.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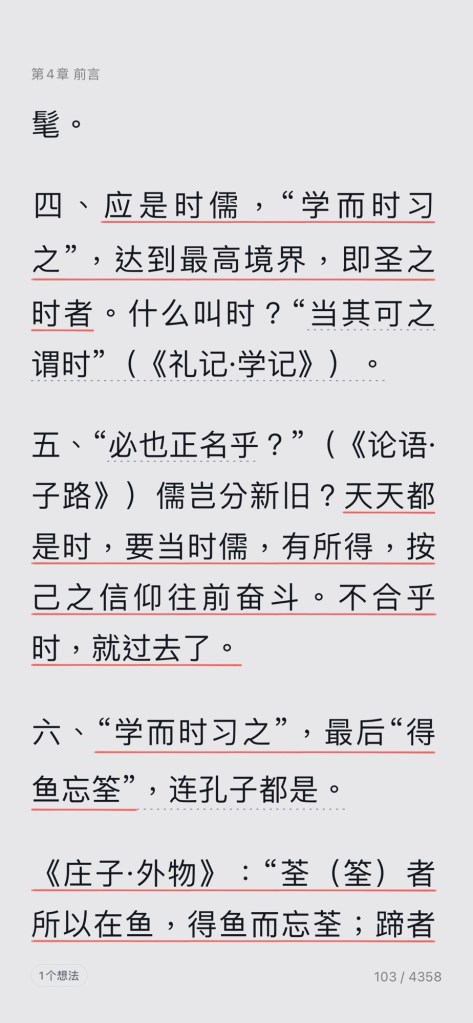

呂榮海:
「時儒」這詞好,新舊會混亂,新的也會變舊,歷史不能停在那裡。林安梧教授即有大作關於「後新儒家」之文及書,推動歷史進程。
有智慧的人短短數語,即可了結紛爭,
有智慧的你伝佈了好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