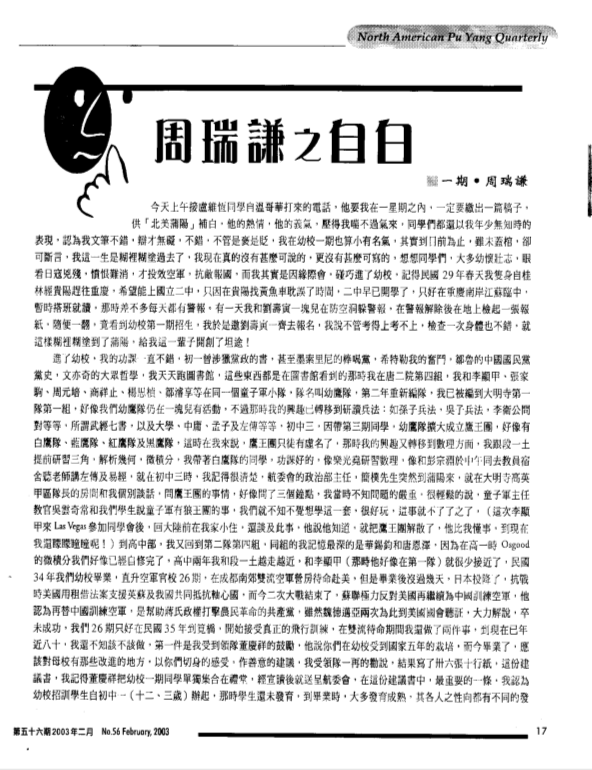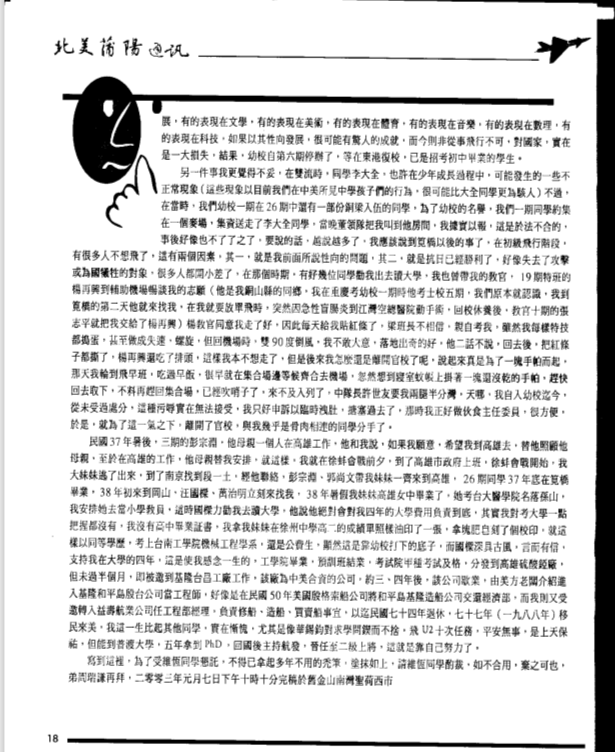我父親在蒲陽空幼與筧橋空官的日子
周隆亨筆抄。
周瑞謙原稿_周瑞謙之自白 20030107 at San Jose, USA
中華民國空軍幼校一期。周瑞謙
今天上午接盧維恆同學自溫哥華打來的電話,他要我在一星期之內,一定要繳出一篇稿子,供「北美蒲陽」補白,他的熱情,他的義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同學們都還以我年少無知時的表現,認為我文筆不錯,辯才無礙,不錯,不管是褒是貶,我在幼校一期也算小有名氣,其實到目前為止,雖未蓋棺,卻可斷言,我這一生是糊裡糊塗過去了,我現在真的沒有甚麼可說的,更沒有甚麼可寫的,想想同學們,大多幼懷壯志,眼看日寇兇殘,憤恨難消,才投效空軍,抗敵報國,而我其實是因緣際會,碰巧進了幼校,記得民國29年春天我隻身自桂林經貴陽趕往重慶,希望能上國立二中,只因在貴陽找黃魚車耽誤了時間,二中早已開學了,只好在重慶南岸江蘇臨中,暫時搭班就讀,那時差不多每天都有警報。有一天我和劉寅壽一塊兒在防空洞躲警報,在警報解除後在地上撿起一張報紙,隨便一翻,竟看到幼校一期招生,我於是邀劉寅壽一齊去報名,我說不管考得上考不上,檢查一次身體也不錯,就這樣糊裡糊塗到了蒲陽,給我這一輩子開創了坦途!
進了幼校,我的功課一直不錯,初一曾涉獵黨政的書,甚至墨索里尼的棒喝黨,希特勒我的奮鬥,鄒魯的中國國民黨黨史,文亦奇的大眾哲學,我天天跑圖書館,這些東西都是在圖書館看到的,那時我在唐二院第四組,我和李顯甲、張家駒、周元培、商祥止、楊思禎、鄒濬享等同在一個童子軍小隊,隊名叫幼鷹隊,第二年重新編隊,我已被編到大明寺第一隊第一組,好像我們幼鷹隊仍在一塊兒活動,不過那時我的興趣已轉移到研讀兵法:如孫子兵法、吳子兵法,李衛公問對等等,所謂武經七書,以及大學、中庸、孟子及左傳等等,初中三,因帶第三期同學,幼鷹隊擴大成立鷹王團,好像有白鷹隊、藍鷹隊、紅鷹隊及黑鷹隊,這時在我來說,鷹王團只徒有虛名了,那時我的興趣又轉移到數理方面,我跟段一士提前研習三角,解析幾何,微積分,我帶著白鷹隊的同學,功課好的,像樂光堯研習數理,像和彭宗淵於中午同去教員宿舍聽老師講左傳及易經,就在初中三時,我記得很清楚,航委會的政治部主任,簡樸先生突然到蒲陽來,就在大明寺高英甲區隊長的房間和我個別談話,問鷹王團的事情,好像問了三個鐘點,我當時不知問題的嚴重,很輕鬆的說,童子軍主任教官吳雲奇常和我們學生說童子軍有狼王團的事,我們就不知不覺想學這一套,很好玩,這事就不了了之了,(這次李顯甲來Las Vegas參加同學會後,回大陸前在我家小住,還談及此事,他說他知道,就把鷹王團解散了,他比我懂事,到現在我還矇矇瞳瞳呢!)到高中部,我又回到第二隊第四組,同組的我記憶最深的是華錫鈞和唐恩澤,因為高一時Osgood 的微積分我們好像已經自修完了,高中兩年我和段一士越走越近,和李顯甲(那時他好像在第一隊)就很少接近了。民國34年我們幼校畢業,直升空軍官校26期,在成都南郊雙流空軍營房待命赴美,但是畢業後沒幾天,日本投降了,抗戰時美國用租借法案支援英蘇及我國共同抵抗軸心國,而今二次大戰結束了,蘇聯極力反對美國再繼續為中國訓練空軍,他認為再替中國訓練空軍,是幫助蔣氏政權打擊農民革命的共產黨,雖然魏德邁亞兩次為此到美國國會聽証,大力解說,卒未成功。我們26期只好35年到筧橋,開始接受真正的飛行訓練,在雙流待命期間我還做了兩件事,到現在已年近八十,我還不知該不該做,第一件是我受到領隊董慶祥的鼓勵,他說你們在幼校受到國家五年的栽培,而今畢業了 ,應該對母校有哪些改進的地方,以你們切身的感受,作善意的建議,我受領隊一再的勸說,結果寫了三十六張十行紙,這份建議書,我記得董慶祥把幼校一期同學單獨集合在禮堂,經宣讀後就送呈航委會,在這份建議書中,最重要的一條,我認為幼校招訓學生自初中一(十二、三歲)辦起,那時學生還未發育,到畢業時,大多發育成熟,其各人之性向都有不同的發展,有的表現在文學,有的表現在美術,有的表現在體育,有的表現在音樂,有的表現在數理,有的表現在科技,如果以其性向發展,很可能有驚人的成就,而今則非從事飛行不可,對國家,實在是一大損失,結果,幼校自第六期停辦了,等在東港復校,已是招考初中畢業的學生。
另一件事我更覺得不妥,在雙流時,同學李大全,也許在少年成長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一些不正常現象(這些現象以目前我們在中美所,見中學孩子們的行為,很可能比大全同學更為駭人),不過,在當時,我們幼校一期在26期中還有一部份銅梁入伍的同學,為了幼校的名譽,我們一期同學約集在一個麥場,集資送走了李大全同學,當晚董領隊把我叫到他房間,我據實以報,這是於法不合的,事後好像也不了了之了。要說的話,越說越多了,我應該說到筧橋以後的事了,在初級飛行階段,有很多人不想飛了,這有兩個因素,其一,就是我前面所說性向的問題;其二,就是抗日已經勝利了,好像失去了攻擊或為國犧牲的對象,很多人都開小差了,在那個時期,有好幾位同學勸我出去讀大學,我也曾帶我的教官,19期特班的楊再興到輔助機場暢談我的志願(他是我銅山縣的同鄉,我在重慶考幼校一期時他考士校五期,我們原本就認識,我到筧橋的第二天他就來找我,在我就要放單飛時,突然因急性盲腸炎到江灣空總醫院動手術,回校休養後,教官十期的張志平就把我交給了楊再興),楊教官同意我走了好,因此每天給我貼紅條了,梁班長不相信,親自考我,雖然我每樣特技都搗蛋,甚至做成失速,螺旋,但回機場時,雙90度倒風,我不敢大意,落地出奇的好,他二話不說,回去後,把紅條子都撕了,楊再興還吃了排頭。這樣我本不想走了,但是後來怎麼還是離開官校了呢?說來真是為了一塊手帕而起,那天我輪到飛早班,吃過早飯,很早就在集合場邊等候齊合去機場,忽然想到寢室蚊帳上掛著一塊還沒乾的手帕,趕快回去取下,不料再趕回集合場,已經吹哨子了,來不及入列了,中隊長許世友要我兩腿半分彎,天哪,我自入幼校迄今,從未受過處分,這種污辱實在無法接受,我只好申訴以臨時瀉肚,搪塞過去了。那時我正好做伙食主任委員,很方便,於是,就為了這一氣之下,離開了官校,與我幾乎是骨肉相連的同學分手了。
民國37年暑後,三期的彭宗淵,他母親一個人在高雄工作,他和我說,如果我願意,希望我到高雄去,替他照顧他母親,至於在高雄的工作,他母親替我安排,就這樣,我就在徐蚌會戰前夕,到了高雄市政府上班,徐蚌會戰開始,我大妹妹逃了出來,到了南京找到段一士,經他聯絡,彭宗淵、郭尚文帶我妹妹一齊來到高雄,26期同學37年底在筧橋畢業,38年初來到岡山,汪國樑、萬治明立刻來找我,38年暑假我妹妹高雄女中畢業了,她考台大醫學院名落孫山,我安排她去當小學教員,這時國樑力勸我去讀大學,他說他絕對會對我四年的大學費用負責到底,其實我對考大學一點把握都沒有,我沒有高中畢業証書,我拿我妹妹在徐州中學高二的成績單照樣油印了一張,拿塊肥皂刻了個校印,就這樣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南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還是公費生,顯然這是靠幼校打下的底子,而國樑深具古風,言而有信,支持我在大學的四年,這是使我感念一生的。工學院畢業,預訓班結業,考試院甲種考試及格,分發到高雄硫酸錏廠,但未過半個月,即被邀到基隆台昌工廠工作,該廠為中美合資公司,約三、四年後,該公司歇業,由美方老闆介紹進入基隆和平島殷台公司當工程師,好像是在民國50年美國殷格索船公司將和平島基隆造船公司交還經濟部,而我則又受邀轉入益壽航業公司任工程部經理,負責修船、造船、買賣船事宜,以迄七十四年退休,七十七年(1988年)移民來美,我這一生比起其他同學,實在慚愧,尤其是像華錫鈞對求學問鍥而不捨,飛U2十次任務,平安無事,是上天保祐,但能到普渡大學,五年拿到Ph.D.,回國後主持航發,晉任二級上將,這就是靠自己努力了。
寫到這裡,為了維恆同學懇託,不得已拿起多年不用的禿筆,塗抹如上,請維恆同學酌裁,如不合用,棄之可也,弟周瑞謙再拜,二零零三年元月七日十時十分完稿於舊金山南灣聖荷西市。